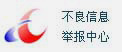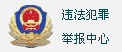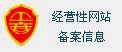○謝佳麗
家家搗米做湯圓,知是明朝冬至天。談及冬至,我的腦海里總會浮現母親在冬至前夕做湯圓的忙碌身影。
記憶里,母親的身影總是忙碌的。家里經營小本生意,因此,母親除了要照顧一家老小,還得時時兼顧百貨店。生活的瑣碎,沖淡了母親對各種習俗禮節的“儀式感”。但唯獨每年冬至的那一頓湯圓,她定要親力操持。因此,我印象中的這一顆顆湯圓,還得是母親自己做的。
做湯圓之前,需要提前兩三天給糯米泡上水。母親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換水,確保糯米不會變質,經過幾番換水浸泡出來的糯米也會更香軟。待糯米浸泡好后,母親會將盛裝糯米的桶運到磨米粉店去。趕上做湯圓高峰期,磨米粉店總要排上一長隊,有些人家會留下名字和聯系方式,讓店家自行安排,待磨好了就通知過來領回。但母親總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定要親眼看著自家的糯米磨成了粉,再親自將其運回。
回到家后,母親也半刻不得歇,她會取出早早洗好晾干的大竹筐,將米粉倒入竹筐里,輕輕攤散開來,放置上一小段時間,待米粉的水分蒸發至似干未干的程度,再動手做湯圓。
做湯圓之時,母親不喜年幼的我們在旁摻和,我們只得遠遠地看著。母親做的湯圓是不下餡料的,沒有繁雜的工序。但她會在一遍又一遍的搓圓之時,口中悠悠緩緩地念叨。我禁不住好奇,曾趁母親專注做湯圓的空隙,走前兩步去細聽,只聽得“小孩一食身體健康長壯實,再食出入平安福氣隨,三食聰明伶俐會讀書;大人一食……”,言語里盡是對全家人的祝愿。幼稚的我,看著母親這般虔誠真摯的模樣,竟在心里暗暗笑話母親這番話說來有何用!
笑話歸笑話,卻絲毫不影響吃湯圓的興奮勁兒。當母親一邊將一碗碗糯香四溢的湯圓端上桌,一邊細心交代小心燙嘴時,我們可完全顧不上她的叮囑,一勺就挖出一顆最大最圓的放到嘴巴里,盡管燙得舌頭在嘴里不住地伸縮擺動,也分毫不減咀嚼品嘗的熱情。隨著一齒咬下,包裹著湯圓的紅糖汁兒瞬間漫延整個嘴巴,再細嚼,糯香味隨即征服味蕾。我們吃得一臉歡喜,母親看著一臉滿足。我們總能在她笑盈盈地注視中將一碗滿滿的湯圓吃光光。
一湯圓,一年歲,流轉間,漸成長。外出讀書時,每逢冬至,學校食堂也會為學生們準備一碗碗湯圓。口味不一,有甜有咸,各憑喜好。吃慣甜湯圓的我,依舊選擇甜口味。欣喜地接過湯圓后,立刻找了個位置坐下來,然后迫不及待地舀起一顆送入口中。只一咬,便皺起了眉頭。仔細端詳勺子中那剩余的半顆湯圓,它還淌著芝麻流沙餡,雖有芝麻香,卻不及記憶里那份糯米香。一時間,一種不知名狀的思緒涌上心頭,我悵若所失地吞咽下后,匆匆起身收拾碗勺離去。爾后幾年冬至,我總婉拒同學共享食堂湯圓的邀約。
兒時的那份糯米香塵封于細碎的時光中,流長靜默,不喧不嚷。
工作后,常覺匆忙。恰逢一年冬至邂逅周末,家婆見空,便張羅著做湯圓。看著她熟稔地做著各種準備工作,我那在流光晃悠的記憶又一次浮現出昔日母親忙碌的身影,一陣熟悉感如花藤順著心底漸漸清晰的身影蔓上心墻,在不失溫暖的冬季里如約綻放。
待一碗碗熱騰騰的湯圓端上來時,孩子們歡呼雀躍。耳畔不時傳來他們富有趣味的談話聲,再看看他們吃湯圓的欣喜模樣,在這聲景交錯間,我竟有些恍惚。腦海中的光陰記錄本在快速翻頁,最終定格在那幀母親做湯圓的畫面上。重溫著昔日母親口中的話語,不甚驚嘆,啊!我竟在為母之后才懂得母親那一聲聲虔誠真摯的祈盼和那一次次親力親為的執著……不禁愧責年幼無知的我竟曾笑話過母親的那份深情。
思憶之際,那份極為熟悉的糯香撫慰著我的心靈,讓我心安神定。齒留的那一縷縷糯香幽幽縈入心間,氤氳化為情,我看著兒子,不語,卻滿眼溫柔。時光清淺,靜默中教會我們愛的真諦。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